|
做一记雷锋,把老三的博转上,照片应该都没有问题。 -- 真的不愿去想这些胯下拉胡琴——扯鸡巴蛋的事来破坏这几天回忆北疆行走的好心情。然而,即使身在北疆纯自然的环境里,我们兄弟间,尤其是三个“六十后”也没能摆脱掉因这些无关问题而引起的碰撞和争执。其实,我们哥几个具是马老板所说的“乖巧好弄的主儿”。我也没资格荣膺老大和老二所封“愤青”或“愤爷”什么的称号,我还经常被我乐队的小弟鄙为“肉食者”呢。 记得从乌市出发一直到第三天在恰尔巴斯草原扎营,我可能让我的兄弟们都感到了压力。虽然,行前就告诫自己与伙伴不谈政治不谈宗教,但当被自然地问道5-12地震的一些情况时,作为身在惊恐中心和参与早期救援的亲历者,可能对人祸的反应更为强烈,对批评缺席下的歌颂更为厌恶。甚而不给身为高知的老大面子,批其“存在即合理”观点为腐朽的历史虚无主义。(是哲学相对主义打开了通向邪恶事物的道路,相对主义是知识分子犯下的许多罪行之一。这是对理性和人性的背叛——波普尔) 现在回想这些,非常地感谢兄弟们给足了我面子。挽回了我们在那么难得的,客观的,直接的,和干净的共同生活中建立的真挚友谊。 记得那天在恰尔巴斯草原的清晨:(周爷也吭哧吭哧地爬了出来,全副武装地跑到对面的山头,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。太阳一上来就很耀眼,照得草原亮闪闪的。周爷在那打坐,远远看去一个红点,觉得是山坡上沁的第一滴血。——竹哥) 当时我是被冻醒了,其实那夜酒劲之后就一直觉着冻,没乍个睡得踏实。天刚亮时,看看侯赛因-王和老马寒刀们睡得正香,没有将要生火做饭的意思,我就起来了。和已经露脸帐外的竹哥点点头,爬到了对面那座已经被第一缕朝霞照亮的山坡之上。坐在温暖的阳光和清甜的空气的包围中,看着这片辽阔的夏季牧场上,一座座毡包随着太阳的照亮而次第升起了袅袅的炊烟,心中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喜乐。吾以为:此时即获得这次北疆行走的第一次开悟——从此,我能非常具体地感触到每一个兄弟的本真与诚善,能真切而清楚的感染到他们性格中的激情与力量。 恰尔巴斯之晨,第一处被照亮的草坡  ![]()
阳光没有照到时,毡包是不会有炊烟升起D  ![]()
骏马已经上来了,没绊哈萨克结(一种可轻松解掉,不会越系越紧,野放时拴马腿的绳结)
 ![]()
阳光照彻了整个恰尔巴斯草原,我的心和马儿一样,沐浴在温暖和祥和中 
(三) 前几天给竹哥做汇报,奉兄命作文的题目是:重返禾木,发呆开悟。其实,在开进禾木的那天夜晚,即竹哥游记中这无法用语言来记录的一个夜晚里,众兄弟及禾木“跑场”歌手赛尔疆一起,在梅花客栈的草地上进行的白酒烛光弹唱,使我获得此次北疆行走中第二次开悟。 (晚饭后马老板叫来草原歌手塞尔江。毫无污染的歌声,从心底唱出,那叫一个豪迈!——竹哥)虽没荣幸到象阿宝那样被央视无比二的“原生态”猴耍,也不可能是“毫无污染草原歌手”了,只是血脉中的律动与大地的联系毕竟紧密些,所以比好多无比二的歌唱家来得自然。  ![]()
(当年的校园歌手,如今成都第一的音乐酒吧老板,操起琴来雄风不减当年——竹哥)进大学才开始弹吉他不假,当校园歌手时却已是很反叛校园文化啰。“成都第一音乐酒吧”——严重d不靠谱!小小芙蓉城里,地上的和地下的玩淫乐滴酒吧,比公厕不知多多少;俺家十年前还算是前驱,当下只能算是渣渣者也。雄风说的AUYUN的吧,与操琴何干,打竹哥板子!  ![]()
(在路上,我和周爷就崔健有一段辩论。周爷说老崔现在的歌牛逼,我说还是早年的好。周爷说那是你现在听不懂,我说不是的。我有个很死板的理论,菜园里的人都知道,把艺术分为两类。一类是与时俱进,但在大的时间尺度上衡量,充其量只能是时代的标签,不能载入艺术史。另一类直指人心,歌唱人的本原,包括他的痛苦和快乐,那些,会一直活下去。比如说,老崔的《花房姑娘》。我们这段路上的争论,没有结论。周爷和赛尔江轮着唱。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,看着我说,下面这首歌为你唱。啊,这是我听过的最打动我的《花房姑娘》,在夜色迷蒙的草原!——竹哥)诗歌自古即是中国文人表达情怀的的一种精华形式,情怀中自然包括人文的修养与真正的社会担当胸怀。老崔就这点牛:无论是用民歌的情调还是愤青的情调,甚或用民工的情调都能表达他自己的这种情怀。其实与听不听得懂,进不进某史都无关系。  ![]()
(这个夜晚无法用语言来记录。永远刻录在这个夜晚上的,是周爷唱的郑钧的那首歌中的一个句子:“生于最冷的冬天/我的名字叫温暖”——竹哥)
感谢竹哥发乎真性情的陶醉与互动,感谢兄弟们忘情的唱和——歌唱的价值永远是双方的表达。今夜是我抱琴唱歌二十多年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纪念日——现在我还说不出它对我未来诗歌生活的影响有多大,但至少今夜使我坚信了歌吟到死的的理由,使我永远不会迷失在当下这个要么扮傻要么装B的“大国文化”里。  ![]()
 ![]()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/8/6 23:59:24编辑过] | 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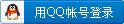


 显身卡
显身卡

 IP卡
IP卡 狗仔卡
狗仔卡







![[原创]7/12新疆行图片日记 [原创]7/12新疆行图片日记](data/attachment/forum/dvbbs/2008-8/200883022562068411.jpg)





